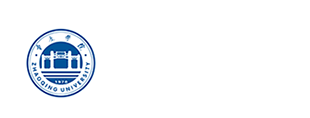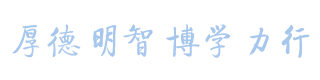广义的岭南包括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、澳门,狭义的岭南文化主要指广东文化。从广义上看,十年来,海南作家韩少功出版了《日夜书》《修改过程》《革命后记》《人生忽然》,孔见著有《海南岛传》。广西则有东西的长篇小说《回响》《篡改的命》,田耳的《天体悬浮》《长寿碑》《金刚四拿》等,凡一平的《上岭村的谋杀》等,朱山坡的《懦夫传》《荀滑脱逃》等,李约热的《人间消息》《景端》等。香港代表作家有董启章、葛亮、周洁茹、程皎旸等人,董启章有《爱妻》,周洁茹有《在香港》《到香港去》《岛上蔷薇》,程皎旸有《危险动物》。澳门作家袁绍珊近作有《拱廊与灵光》《爱的进化史》。鉴于广东文学在岭南具有代表性,以及笔者对广东文学的熟悉,本文的岭南文学以狭义的广东文学为中心。李怡在《“地方路径”如何通达“现代中国”》中指出:“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,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,许许多多的‘地方路径’,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‘中国经验’……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,而更大的整体的‘大传统’却不是一成不变的,‘大传统’的更新和改变显然与地方经验的不断生成关系密切。”十年来岭南文学是如何走出其“岭南路径”的?
文学中的岭南
近十年广东籍的代表作家,在纯文学方面有“40后”刘斯奋、林贤治;“50后”郭小东、筱敏、张梅、叶曙明、马莉、唐德亮;“60后”陈陟云、世宾;“70后”黄礼孩、厚圃、黄金明、刘迪生、洪永争、彤子(蔡玉燕);“80后”林棹、陈崇正、林培源、陈诗哥、陈再见、唐不遇;“90后”路魆、梁宝星、索耳等。“70后”的葛亮是广东省作协会员、广州市作协副主席,所以本文把他归入广东作家队伍,也无不可。网络文学方面,则有阿菩、玄雨、求无欲等。但是,我们遗憾地发现当下的广东籍作家,就其深度和影响而言,暂不如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界的广东籍学者,如饶宗颐、詹安泰、罗宗强、杨义、洪子诚、陈平原、温儒敏、方汉奇、吴承学、饶芃子、林岗,诸如此类,都是举足轻重的学者。
广东籍作家只是一种身份,而要探讨十年来广东文学的“岭南路径”,还需要了解以岭南为题材的广东文学,这已经不局限于广东籍作家,而是涵盖在广东进行创作的所有作家。
近十年以岭南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为数不少,可见广东作家对岭南的关注甚至热爱,毕竟,这涉及作家所处的文化场域与生存体验。这些创作大概可分为几类:一是以岭南乡土为题材。如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林棹的《潮汐图》、陈继明的《平安批》、吴君的《晒米人家》、郭小东的《铜钵盂》、陈崇正的《半步村叙事》、洪永争的《摇啊摇,疍家船》《浮家》、厚圃的《拖神》、盛琼的《光阴渡》、林培源的《小镇生活指南》、梁宝星的《金属婴儿》、钟道宇的《紫云》《仙花寺》等小说,林贤治的《通往母亲的路》、熊育群的《双族之城》、林渊液的《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》、杨芳的《守河者》等散文。另外,魏微的小说《沿河村纪事》虽是以广西为背景,却也是广义的岭南乡土题材。
二是以岭南都市为题材。如邓一光的《如何走进欢乐谷》《离开中英街需要注意什么》、吴君的《华强北》、张欣的《千万与春住》《黎曼猜想》、盛可以的《女佣手记》、蔡东的《月光下》、南翔的《老桂家的鱼》、王威廉的《你的目光》、陈再见的《出花园记》《回县城》、盛慧的《闯广东》、彤子的《陈家祠》、王十月的《人罪》、阿菩的《十三行》等小说,郑小琼的《女工记》、杨克的《杨克的诗》《精神地图》等诗集,曾平标的《中国桥》、陈启文的《为什么是深圳》、丁燕的《工厂女孩》《低天空: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》、杨黎光的《横琴》、叶曙明的《广州传》、黄国钦的《潮州传》等报告文学,彤子的《生活在高处——建筑工地上的女人们》、塞壬的《匿名者》《沉默、坚硬,还有悲伤》《无尘车间》等散文。
三是以岭南人物为题材。如熊育群的《钟南山:苍生在上》、杨黎光的《脚印——人民英雄麦贤得》、刘迪生的《大河之魂: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》等报告文学。
岭南作家,无论是否广东籍,他们所处的文化场域与生存体验,影响了其文学创作,这是“岭南路径”的外在层面,而在此基础上,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书写岭南,以许许多多的岭南故事、岭南人物、岭南风格、岭南精神,构成了对岭南的再生产,对岭南的活化与再造,这是“岭南路径”的内在层面。在此意义上,地方生产出文学,文学也生产出地方,二者相辅相成,交织互渗。
岭南的文学
“岭南路径”不只指涉“文学中的岭南”,也指涉“岭南的文学”。前者主要是就作家身份、书写内容而言,后者则在整体上,主要指向岭南文学的新收获和影响力,二者合起来,才构成完整的“岭南路径”。其实,写不写岭南(地方),并非“岭南路径”(地方路径)的必经之路,有的作家的创作甚至刻意与生存环境、生活体验保持距离,而注重更为内在的生命体验、历史思考与存在叩问,注重视角、语言、形式、叙事的突破,这种更为独立的“个人路径”,才是一个作家所应开拓的。毕竟,文学首先体现为“个人路径”,然后才逐渐形成“地方路径”,“个人路径”才是更为关键的,如果一个作家创作了不少地方题材的作品,但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、独特体验、独特构思,那么,这时候“地方路径”对作家无疑是一种障碍,使他无法跳出具体的地方去审视更为广阔的世界与历史,无法去挖掘更为深刻的存在内涵,无法进行更为独特的美学创造。所以,有时候抛开所处的地方,书写遥远的地方,甚至抛开具体的地方,虚构虚无之境,却赋予了作家一种创作的自由与独立。例如郭爽不写广东,而以贵州家乡为题材写作了系列小说;王威廉也很少写广东,而以思辨性对荒诞存在进行书写;庞贝不写广东,创作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悬疑小说,等等。
就十年来的岭南文学而言,传统的几大文体,诸如在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方面都收获颇丰。
十年来的岭南小说,体现了岭南文学的新收获和影响力。主要有三类,即都市题材小说、军事题材小说和科幻或荒诞小说。首先是都市题材小说。葛亮的《飞发》写的是一个关于港式飞发与沪式理发的文化碰撞交流的故事,更是一个关于“头发”与人生的故事。在父子两代人那里,在不同的场域,头发已不仅仅是头发,更隐喻着香港文化的混杂,时代的变迁与心灵的变迁。更为特别的是小说的结构与考据,葛亮运用学者的思维对“飞发”的传统进行细密的考据,并将考据运用于小说的结构之中,尤其是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偶数章节,都是关于“飞发”传统的考据,如《楔子:“飞发”小考》《贰:“飞发”暗语》《肆:有关“三色灯柱”的典故》,继而将考据与故事交织,让《壹》《叁》《伍》《柒》《尾声》等奇数章节构成完整的故事章节,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跳转,在学术与文学之间跳转,在貌似无情、不动声色的考据章节之后,进入了包含情感体验的故事章节。换言之,这是关于“飞发”的知识与情感的故事,与“飞发”知识对应的是考据,与“飞发”情感对应的是故事,如此,就将“飞发”的形而上层面与形而下层面打通,而这种在考据与故事之间的“移动”,暗中隐喻了香港“新移民”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的“移动”,无形中体现了香港文化的混杂特质,也折射了“多情却被无情恼”的存在哲理。
军事题材小说方面,岭南文学的新收获有邓一光的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熊育群的《连尔居》《己卯年雨雪》,庞贝的《乌江引》,这几部小说都下足了考据的功夫。邓一光的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有三点创新:一是题材创新,以香港十八日保卫战为焦点;二是空间创新,聚焦于日军设于丛林中的D俘虏营,这是不同于一般的战场空间的鲜为人知的战争空间;三是叙事创新,以战后法庭审判的方式结构这部长篇小说,设置了一种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。熊育群的《己卯年雨雪》以1939年长沙会战、营田屠杀为背景,主人公祝奕典夫妇和日兵武田夫妇在战争之前,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区别。但战争来临,这一切急剧变化,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,小说写的是祝奕典与千鹤子之间仇恨与宽恕的故事。该小说非常注重细节,熊育群为此查阅了大量书刊,一方面使得小说具有战争的真实,另一方面却又具有人心的真实。前两部小说关注抗战,庞贝的《乌江引》则关注长征。该小说聚焦于长征中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,即以“破译三杰”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。他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,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,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、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而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。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范例,这是部以其新题材、紧张感与专业性胜出的作品,令人拍案叫绝。
在科幻或荒诞小说方面。岭南文学的新收获有王威廉的《野未来》、陈崇正的《黑镜分身术》、吴岩的《中国轨道号》、庞贝的《独角兽》、黄惊涛的《引体向上》、王十月的《如果末日无期》等科幻小说,也有王威廉的《倒立生活》《没有指纹的人》、陈崇正的《半步村叙事》、路魆的《暗子》、梁宝星的《金属婴儿》等荒诞小说。客观而言,科幻是另一种现实,是用科幻的形式表述现实体验与现实思考。与此同时,科幻也是一种荒诞,这种荒诞来源于对现实的幻想或幻象。但是,创作科幻小说,也需要有专业支撑。吴岩的科幻小说《中国轨道号》就表现出一种专业性,但如何在专业性之外呈现更宽阔的现实思考、更深入的人性挖掘、更巨大的历史隐喻、更新颖的形式与人物的创造,甚至对未来科学的想象,应是科幻小说作家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。
广东的诗歌氛围十分浓郁,多次举办广州新年诗会、诗歌音乐会、诗歌节、诗歌周、民间诗歌奖等,诗歌群落也较多。岭南诗人的独立性或民间性很强,如东荡子、陈陟云、世宾、马莉、郑小琼、黄礼孩、梦亦非、嘉励、林馥娜、冯娜、凌越、杜绿绿、陈会玲等。马莉曾一语中的:“大诗人是忧患深重的,而小诗人多是享乐、逐利与苟且的。在诗歌的书写活动中,我尊重他人的选择,我从不用内心的尺度去衡量他人,我只衡量自己。”(见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2021年第1期)
此外,十年来岭南文学中的报告文学或非虚构作品收获不小。不仅有李兰妮的报告文学《野地灵光: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》,这是她继2008年《旷野无人: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》之后的重要收获;还有陈启文的报告文学《命脉——中国水利调查》《袁隆平的世界》《大河上下:黄河的命运》等,这是他在《共和国粮食报告》之后继续努力前进的见证。另外,还有熊育群的《钟南山:苍生在上》《第76天》,叶曙明的《广州传》,以及上面提及的曾平标、丁燕、杨黎光、刘迪生、西篱等人的报告文学。当然,也不能忘记黄灯的非虚构作品《大地上的亲人》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等。
综上所述,无论是“文学中的岭南”还是“岭南的文学”,都是从“岭南路径”(地方路径)入手,而不只是着眼于“岭南路径”(地方路径)。因为岭南文学一般比较传统,走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路线居多,所以有必要超越“岭南路径”,进入更为内在的个人路径、更为广阔的存在路径、更为新颖的形式路径,以此开拓世界眼光。